第一章弄堂深处的青梅时光1940年的上海,秋老虎还没退去,
霞飞路的梧桐叶却已染上浅黄。苏念卿抱着一本线装的《漱玉词》,坐在弄堂口的石墩上,
指尖划过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”的字句,耳边是电车“叮当”的**,
混着隔壁裁缝铺的剪刀声,还有陈砚秋跑过来时,帆布鞋踩在青石板上的“哒哒”响。
“念卿!别老看这些愁人的词,跟我去外滩逛逛?”陈砚秋喘着气,额角沾着汗,
白衬衫的袖口卷到小臂,露出结实的手腕——那是他在军校练刺杀磨出的茧子。
他比苏念卿大两岁,去年刚考进中央军校上海分校,眉眼间还带着少年的清亮,
却已多了几分军人的挺拔。苏念卿合上书,抬头看他,阳光落在她的发梢,
映得耳尖微红:“不去了,阿娘让我早点回去做饭。”她顿了顿,又小声补了句,“再说,
外滩最近不太平,日本人的巡逻车总过。”陈砚秋摸了摸口袋,掏出一颗水果糖,
剥了糖纸递给她:“怕什么?有我呢。等我毕业了,就去前线打鬼子,把他们都赶出去,
到时候咱们再去外滩,想逛多久逛多久。”苏念卿接过糖,含在嘴里,甜意漫开,
却压不住心里的慌。这半年来,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,日军的据点越建越多,
街头的“良民证”检查也越来越严。她见过邻居张叔因为没带良民证,
被日军打得头破血流;也见过深夜里,宪兵队的卡车呼啸而过,带走不知多少人。她怕,
怕陈砚秋真的去前线,怕他再也回不来。“砚秋哥,”她攥着衣角,声音轻得像风,
“能不能……别去前线?找个安稳的工作,不好吗?”陈砚秋蹲下来,看着她的眼睛,
手指轻轻拂过她眉间的细纹——那是她最近总皱眉才有的:“念卿,我是军人,国难当头,
怎么能躲?你忘了,我们小时候在城隍庙许的愿,说要让中国人都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
现在这个样子,我不能逃。”他说起小时候,苏念卿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那时候他们都才七八岁,跟着大人去城隍庙,她许愿要永远和砚秋哥在一起,
他许愿要当大英雄,保护她,保护所有人。那时候的天很蓝,城隍庙的香火气很浓,
他们以为未来都是好日子,从没想过,长大后要面对这样的兵荒马乱。晚饭时,
苏念卿的父亲苏先生叹了口气,把报纸推到陈砚秋面前:“北平那边打得厉害,日军增兵了,
你们军校是不是要调人过去?”陈砚秋放下筷子,点了点头:“校长说,下月初就出发,
去北平支援。”苏母的手顿了一下,碗里的汤洒了出来:“这么快?就不能……再等等?
”“阿姨,等不了了。”陈砚秋的声音很沉,“北平是重镇,丢了就完了。我必须去。
”苏念卿低着头,扒着碗里的饭,眼泪掉进碗里,混着米粒咽下去,又咸又涩。她知道,
她留不住他,就像留不住秋天的梧桐叶,留不住上海的好时光。出发前一天,
陈砚秋把苏念卿约到外滩的和平饭店前。那天没有太阳,风有点凉,黄浦江的水泛着灰光,
远处的外国军舰像幽灵一样停在江面上。陈砚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,打开,
里面是一枚银质的婚戒,戒指内侧刻着“秋”和“卿”两个字。“念卿,”他的手有点抖,
把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,“这个你先戴着,等我打完仗,就回来娶你。我们去北平,
看那里的冬雪,长城上的雪,一定比上海的好看。”苏念卿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,
她抱着陈砚秋的腰,把脸埋在他的衬衫里,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皂角味:“砚秋哥,我等你,
不管多久,我都等你。你一定要回来,一定要带我去看北平的冬雪。”“好,我一定回来。
”陈砚秋抱着她,声音发颤,“你照顾好自己,照顾好叔叔阿姨,别担心我。我会给你写信,
每天都写。”第二天,陈砚秋跟着部队走了。苏念卿去车站送他,看着火车慢慢开动,
陈砚秋从车窗里探出头,挥手喊:“念卿,等我!”她追着火车跑,直到再也跑不动,
手里还攥着他昨晚给她的手帕,上面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。火车消失在远方,
苏念卿站在车站的寒风里,看着手里的婚戒,心里一遍一遍地说:“砚秋哥,我等你,
我等你回来带我看冬雪。”第二章烽火里的断信与误解陈砚秋到北平后,
第一时间给苏念卿写了信。信里写了北平的秋景,写了部队的生活,写了他对她的思念,
最后说:“等冬天来了,我就去长城看雪,替你先看看,好不好?”苏念卿收到信时,
正在给父亲缝补衣服。她拿着信,看了一遍又一遍,眼泪掉在信纸上,晕开了字迹。
她立刻回信,写了上海的近况,写了弄堂里的梧桐叶落了,写了她每天都在等他的信,
最后说:“砚秋哥,你要照顾好自己,别受伤,我等你回来。”接下来的几个月,
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。陈砚秋的信里,有时会提到打仗的凶险,说身边的战友牺牲了,
说他被子弹擦过胳膊,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,说等胜利了,
就带她去北平的胡同里吃冰糖葫芦,去颐和园划船。苏念卿的信里,总是报喜不报忧,
说父亲的身体好了些,说弄堂里的邻居都很照顾她们,说她把他的照片放在枕头边,
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。可到了1941年冬天,信突然断了。苏念卿等了一个月,
没收到陈砚秋的信;等了两个月,还是没有。她去邮局问,邮局的人说,前线的邮路断了,
很多信都送不出去。她又去问陈砚秋的同学,同学说,最近北平打得很凶,
陈砚秋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了,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苏念卿的心沉了下去。
她每天都去车站,去邮局,希望能收到陈砚秋的信,哪怕只是一张纸条,说他还活着。
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开春的时候,苏念卿的父亲突然病重,咳得厉害,
医生说需要进口的西药,可那时候上海被日军封锁,西药很难买到,价格也贵得吓人。
苏母到处借钱,头发都愁白了,还是凑不够钱。就在苏念卿走投无路的时候,
邻居王阿姨给她介绍了一个人——张先生,做布匹生意的,妻子去世了,没有孩子,
为人老实,愿意帮她父亲治病,条件是娶她。苏念卿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父亲,
又想起杳无音信的陈砚秋,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她想等陈砚秋,可父亲等不了了;她想拒绝,
可她没有别的办法。“我答应你。”她对张先生说,声音很轻,却带着决绝。
婚礼办得很简单,只有几个亲戚朋友。苏念卿穿着红色的旗袍,却没有一点喜悦,
她摸着无名指上的婚戒,心里一遍一遍地说:“砚秋哥,对不起,我等不了你了,
我只能这样做。”婚后,张先生对苏念卿很好,帮她父亲治好了病,对她也体贴。
可苏念卿心里,始终有一个角落,是属于陈砚秋的。她把陈砚秋的信和照片,
放在一个铁盒里,藏在衣柜的最深处,只有在深夜,才敢拿出来看,看着看着,就泪流满面。
而陈砚秋那边,并不是不想写信。1941年冬天,他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,
打了三天三夜,他中了弹,被战友救了出来,送到后方医院。在医院里,他一直昏迷,
醒来时,已经是开春了。他第一件事就是给苏念卿写信,可医生说,他的手受了伤,
暂时不能写字。他只能让战友帮忙写,写了很多信,说他还活着,说他很快就会回去见她。
可那些信,都没能送到苏念卿手里。日军为了切断前线和后方的联系,炸毁了邮路,
很多信件都被烧毁了。陈砚秋等不到苏念卿的回信,心里很着急,他问战友,战友说,
可能是邮路还没通,再等等。1943年,陈砚秋伤愈归队,继续在北平打仗。
他还是坚持给苏念卿写信,每次路过邮局,都要去问有没有她的回信,可每次都是空欢喜。
他开始担心,是不是苏念卿出了什么事,是不是上海被日军占领,她不在了。有一次,
他遇到一个从上海来的伤兵,赶紧问他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苏念卿的女孩,
住在霞飞路的弄堂里。伤兵想了想,说:“霞飞路?我知道,那里有个苏**,
去年嫁给了一个做布匹生意的张先生,听说过得挺好。”陈砚秋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
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他不敢相信,苏念卿竟然嫁人了?她忘了他们的约定?忘了北平的冬雪?
他回到部队,把苏念卿的信拿出来,一遍一遍地看,信里的“我等你”还在,
可她已经嫁给别人了。他把信烧了,把那枚准备送给她的、和他自己戴的成对的婚戒,
藏在贴身的衣兜里。他想,既然她已经幸福了,那就别去打扰她了,他一个军人,
随时可能牺牲,给不了她安稳的生活,她嫁给别人,或许是对的。从那以后,
陈砚秋再也没给苏念卿写过信。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打仗上,变得沉默寡言,
只有在看到长城的时候,才会想起那个约定——带她去看北平的冬雪。
第三章胜利后的擦肩而过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到北平,
陈砚秋正在长城脚下站岗。他听到广播里的声音,愣了半天,然后突然哭了出来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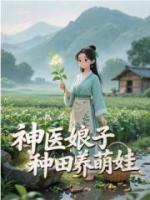 神医娘子种田养萌娃
神医娘子种田养萌娃 妻子的钢琴课
妻子的钢琴课 婚礼直播我被绿视频,让拜金未婚妻和情夫全网社死
婚礼直播我被绿视频,让拜金未婚妻和情夫全网社死 错认爹地后,锦鲤崽崽靠玄学爆红全家
错认爹地后,锦鲤崽崽靠玄学爆红全家 彼岸花开:都市引魂者的宿命奇谈
彼岸花开:都市引魂者的宿命奇谈 慕晚时萧景铄
慕晚时萧景铄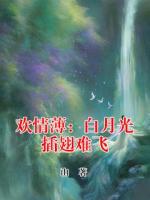 欢情薄:白月光插翅难飞
欢情薄:白月光插翅难飞 肖像师的诡异委托
肖像师的诡异委托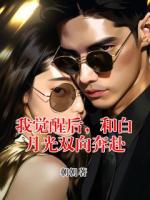 我觉醒后,和白月光双向奔赴
我觉醒后,和白月光双向奔赴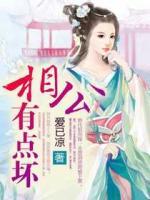 相公有点坏
相公有点坏 恶魔宝宝:敢惹我妈咪试试!
恶魔宝宝:敢惹我妈咪试试!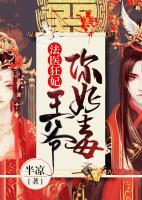 法医狂妃:王爷你好毒
法医狂妃:王爷你好毒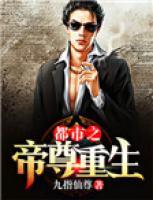 都市之帝尊重生
都市之帝尊重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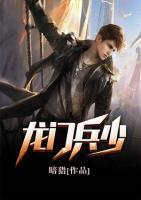 龙门兵少
龙门兵少 娇养小厨娘
娇养小厨娘 仙岛归来,从救下美女总裁开始
仙岛归来,从救下美女总裁开始 贫道专治各种不服
贫道专治各种不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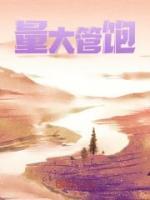 量大管饱
量大管饱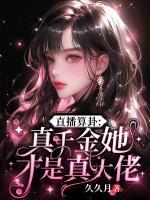 直播算卦:真千金她才是真大佬
直播算卦:真千金她才是真大佬 带崽相亲,闪婚老公竟是千亿大佬
带崽相亲,闪婚老公竟是千亿大佬 花都大仙医
花都大仙医
我平时很爱看小说,但一直没有找到很心仪的,直到看完《等不到的冬雪》以后,我彻底被这部小说圈粉了,作者郁鹂娜的思路很清晰,让人看完一遍还想再看第二遍,真心不错。